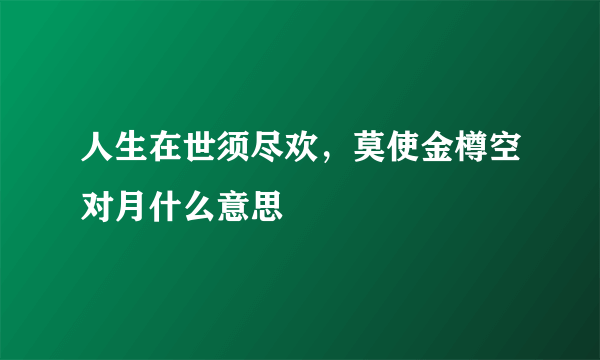求《交响人生》观后感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刚看完《交响人生》。看到三分之二还在奇怪,明明拍的很欢乐,哭点在哪里。曾经的音乐家们挤过餐厅的大门,吵嚷着要钱;做着共产主义复辟的梦的党棍;排练时带着熨斗开始熨衣服的吉普赛大妈;到犹太老头的儿子抱怨没有带中国手机来巴黎贩卖时我不厚道的笑抽了。直到柴小协开始,安娜-玛瑞的琴弓搭上琴弦,第一个音符划过空气,撕裂三十年的时光。那三十年间生存本身化身冰川,缓慢而决绝的从他们身躯上碾过,生生的剥下他们的血肉,优雅、尊严乃至音乐,一一随着冷酷的冰流向山脚,温润的土壤被剥蚀干净,只剩粗陋的岩石兀立在那里,那是他们尖锐而张牙舞爪的硬邦邦的骨。其实他们依旧感知的到那被剥离的曾经的自己在心底留下的那一条又一条终碛垄,但无力也懒得再去回头俯瞰,生存太重而生命太轻,要存活必须放弃那些柔软而美好的累赘。他们把灵魂埋在那终碛垄里,只剩身躯在世界上无目的的爬行与生存。那一声琴声从地下涌出,如温热的泉,在冰的世界里融出一条黑色的裂纹,那是冰封的时光之门悄悄开启的缝隙,幽灵回到人间,已逝的丽娅悄悄的还魂,附身于女儿,活着的幽灵们各归其位,一起来演奏这未完的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泪水蓦地滑落,不是为了剧情。其实全剧并无悬念可言,安娜一出镜,我猜她可能是安德烈的女儿,到安德烈在餐厅里对安娜讲起丽娅的往事,改猜她是丽娅的女儿,果然中的。我甚至感觉,导演本人也并没花心思来构造悬念,他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线索,让这最后一曲小协响起。俄罗斯这个国家,总让我感到一种撕裂与矛盾。理性上该去恨,它给中国带来太多太深重的苦难,夺我土地辱我国民,扶植匪徒颠覆我合法政府,将红祸输入中国遗毒至今。可感性上,却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这样的故事总不绝于耳,诸如俄罗斯人在贫困潦倒时依然去听音乐会、火车上的小贩坐在走私来的货物上手捧一本书细细阅读之类。对于同为红祸所戕害的普通俄罗斯人,我怀有的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可这不是我想谈的。毕竟,无论是红祸也好,纳粹也好,以这些反人性的极权体制为主题的电影作品和文学作品都太多,远比这部电影更深刻、更通透、更震撼的也比比皆是。我也不想更励志的谈梦想与坚持之类(内心对励志题材是抵触的),总觉得一旦开始从励志角度观赏一部艺术作品,这部作品就被庸俗化了。这部电影更触动我的主题,是对音乐与人本身的关系的一种探问。安德烈在片中坦言,他庇护犹太的乐师,不是因为良知与正义,而是因为自私——他需要他的乐师们,演奏出那最完美的柴小协。他需要丽娅完美的和弦,仅仅是和弦本身。这简单的执念支撑他穿越三十年的时光,一有机会重新演奏,便拼命将故人们一一聚齐,哪怕是仓皇的在巴黎街头一个个捉人,也要演奏到底。最终柴可夫斯基的旋律也让这些活死人们一个个活过来,找回当年的声音。联想起类似题材的《天堂里的小提琴》。集中营里犹太人们已经被折磨成行尸走肉,纳粹军官为找回杀死活生生的人的乐趣,请来小提琴手为他们演奏。等到他们一个个重新找回自己的灵魂后,再来一场屠杀。音乐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当一个人只能处于底线的生存时,这样的力量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一部电影一本书,给出两个看似相反却殊途同归的答案。人类在漫长而残酷的演化史里挣扎着向上,从稚弱小草长成参天大树,生物意义上的生存已经仅仅是大树的根基,对人们而言,更重要的是离天空更近、离大地更远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之为人而不仅仅是一种动物的标志。悲哀的是,这些也是最脆弱和最不确定的部分,一旦风暴袭来,大树折断,只有根基还可以留在泥土里。我们脆弱无力的生命,在强大的外力面前没有丝毫抵抗力。我们作为人的一切标志,在基本的生存面前都必须一一的抛却。换个说法,我们身为“人”的属性与“人”的实体之间,并不是百分百重合的,选择当一个“人”与选择以“人”的实体生存,完全有可能存在矛盾。这种矛盾是一切哲学命题的根源。对于常态下的生命,这种矛盾可能仅仅是一条淡淡的忧伤的裂隙;但在极端情况下,这裂隙会撕裂成巨大的鸿沟,二者必须择一,要么以“人”的属性死去,要么以“人”的实体存活。极权与音乐(或者死亡与音乐)的主题,恰恰是这种矛盾的一种集中而直白的体现。回到这部电影里,极权的暴政下,丽娅与她的同事们各自失去了生之为人的一部分,丽娅失去的是“人”的实体,其他的乐师们失去的是“人”的属性。随着一首柴小协,他们各自找回了一个完整的自己。丽娅的肉身已然死去,但她的生命得以在安娜-玛瑞身上延续;其他乐师们则随着旋律回溯找回了自己作为音乐家的尊严与优雅。这样一个失而复得的过程是温暖的。相比之下,《天堂里的小提琴》更冰冷与绝望,纳粹军官还给那些犹太人们“人”的属性,为的仅仅是杀死一个完整的“人”的快感。写到这里文字渐自干涸,无以为继。虽然言犹未尽,但也许就此搁笔恰恰好,既是对电影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