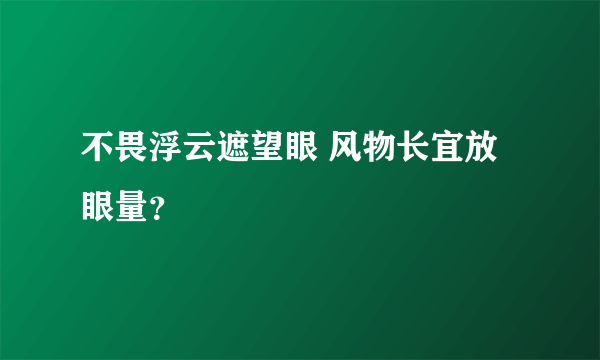“不畏金刚怒目,只怕菩萨低眉”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菩萨低眉,金刚怒目 《华严经》云:「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世界中,无法不造作。」,说明人心是能善、能恶、知善、知恶的本源。心,既是导引肢体语言行为的「善恶」,也就能表现人性本能与心理行为的「爱恨」。因此「爱」与「恨」是一体的两面,人为了能满足私欲,就有无限的「贪爱」,一旦私欲难满时,「忿恨」就随之而起。因此,从「自我」的观点来看,「爱与恨」是心理的,也是本能的,而爱与恨往往是人间的苦因,烦恼源头。然而,爱与恨虽然是相对的,但也不尽然是绝对的;也就是说,「爱」未必全然是好的,而「恨」也未必都是不好的,唯有「大爱」和「大恨」,以公益为出发,「爱」与「恨」才有正面与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大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菩萨,是一种无污染、纯净的爱,如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大恨是大意志、大威德,是一种瞋恨的升华;也就是愤怒金刚、威摄邪魔的公义伸张。《涅盘经》中,指出如有人危害社会而使社会受灾难时,菩萨会予以制止,阻其作恶,而菩萨已发愿承挑制止恶人的一切结果。「爱」与「恨」有不同的层次与境界,於佛法而言,不落爱恨是超脱的菩萨,有爱无恨的是世间的圣贤,而人世间的凡夫,是「有爱有恨」的。既然,有爱有恨,「菩萨低眉,金刚怒目」,怀抱「慈悲心」的爱与恨,才是现代人应有的情怀。一切要爱得有意义,也要恨得有道理,内心清明自在的「爱与恨」,才是无挂碍的「爱与恨」。《维摩经》说:「菩萨是向众生中求的。」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佛之所以成佛,是因为有众生让他度,有众生让他作功德,所以,菩萨成为伟大的救世者,佛能完成福德和智慧的大圆满者。如果没有众生让他们度,让他们服务,那他们就不能成为菩萨,不能成为佛了。芸芸众生并没有给菩萨与佛任何回馈,在没有任何回馈之中,他们本身已经完成了自我成长、自我建设、自我成就,从这个观点看,「给人方便」就已经成就自己,实在很划算。《梵网经菩萨戒本》说:「应代一切众生,受加毁辱,恶事向自己,好事与他人。」而在《瑜伽菩萨戒本》却规定菩萨不得不护雪(护持雪耻)外来的「恶声、恶称、恶誉」。这是说,为了爱护众生,应代众生受怨受辱;为了维护三宝,应该护雪恶意的中伤。再说,菩萨对众生,当存慈悲心,但在必要时也应以威折的方法,使得众生驯服。所以,菩萨若见到有些人应加呵责,治罚、驱逐、默槟(不和他说话),而不如此处置的,便犯戒。菩萨度众生,虽有只为众生而不为自利的存心,但从佛法的常理上说,总以健全了自己之后,更容易发挥度他的效果。身教总比言教更能够感人,身教配合了言教,乃是佛法化世的常轨。所以,作为一个佛弟子,他本身的言行,必须要一致。他的言行必须是:说佛所应说的话,作佛所应作的事。然后才可谈到影响他人而摄化众生。从个人的自我教育与自我修持,而到度脱众生,这是上求佛道以自度,下化众生以度他的菩萨之道。但是菩萨的精神,绝不是只在於自度的工夫之中,乃是於一边修行自度,同时也要从事於兼度众生的工作。并且他们在基本观念上,没有自度的存心。他们之将自己健全起来,目的是在利用健全的自己以度众生,而不是要使自己首先度脱生死的苦海。个人健全之后,便可影响他的家人亲友,感化他的家人亲友,进一步影响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形成一种佛化的风气,造成佛化社会的人间净土,这是菩萨行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作为一个菩萨,他的境界越高,他所能够影响的范围也就越大;他的悲愿力越大,他能应化的众生类别也就越多。一般的菩萨,仅能在人间的文明地区教化;圣位的大菩萨们,却能不离於圣位的本处而随类示现,乃至深入最低下的众生如傍生、饿鬼、地狱道中,应化救济。但是,要度众生,单凭一股宗教狂热的情绪是不中用的,宗教的狂热,固然能使人们生出赴汤蹈火的勇气,去宣传、去辩论、去冲锋、去陷阵、去战斗、去牺牲,但那决计不能持久,也决计不能产生深远的良好影响。佛教,是以服务社会为菩萨道的表徵,佛在往昔的无数生中,以种种身分、种种形态、种种方式,深入种种的族群中,每每能居王的地位。所谓王,就是领袖,那些领袖的地位,不是仗武力打得来的,全是以服务大众的道德价值所感召而致的,因为,唯有真正能为大众谋幸福的人,才是最够资格做大众领袖的人,才是最能赢得众望所归并心悦诚服的人。因此,一个理想的居士,虽然不必在任何场合都要以领袖的姿态出现,至少,他该是受到任何场合所欢迎的人,乃至是能受到任何场合所尊敬的人。一个佛教徒的本色,应该是多尽义务,少享权利,才能获得他人的爱戴。因此,佛为统摄一切团体——社会的要求,说了四种德目,称为四摄法。摄是统摄和摄受,也就是领导或化导的意思。所谓四摄法,就是领袖人物所不可缺少的四种处世方法,切实地做好了四摄法的工作,便能感化群众,也能领导群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