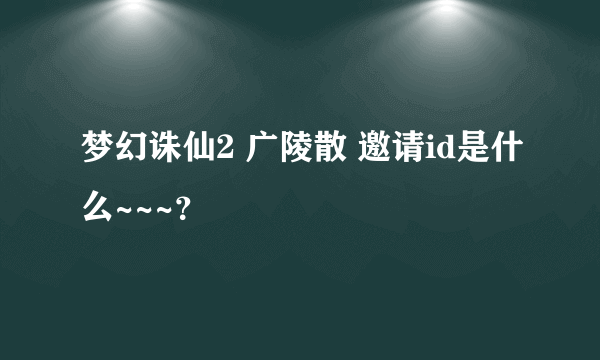嵇康之死与广陵散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世说新语·雅量》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 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文大意是说嵇康被司马氏处以死刑于东市(即古代处以极刑的地方)时神态不变,悠闲大度,毫不畏惧,只是为自己的《广陵散》失传而遗憾的情景。文中“勒固”据《世说新语考释》(吴金华 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认为是用作同义复词,表示固守,吝啬,舍不得之意。比如《玉篇》:“勒,固也。” 翻开《世说新语》,跌入一个玄乎晕乎的时代,嵇康留给后人的感慨似乎最多,前人留给后人关于这些感慨的资料也就很多了。特别是嵇康临死的神态,为千古传颂。嵇康之死的本末,据《魏氏春秋》记载:“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晋书》说他“顾视日影,索琴弹之”。 甚至现在有些后人描述:“公元262年一个夏日的傍晚,落日的余辉将洛阳东市刑场染成橙色。风儿轻轻,琴声悠扬,围观的人群屏气慑息,谛听着神秘的旋律、生命的绝响。抚琴人是被司马昭画了红圈的魏晋名士嵇康。”似乎就是当时的场景了。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以古人的描述想象古人,比如简单的相信嵇康的当时的社会地位,加上《世说新语》的片面神化,以及《晋书》《魏氏春秋》相互引用。导致了很多后人的误解。“嵇康活得坦荡,走得潇洒,他没有过多的牵挂,只是想到《广陵散》将要失传感到有点遗憾。嵇康这极富诗意极具美感的临终一叹,将生命的旗帜插上了人类美学的高山之巅。”之类的言辞。 嵇康是否活得坦荡,是否走得潇洒——这是濠墚之辩,我们不是嵇康,自然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毕竟。我们不是嵇康。但是我么客观的把整个事件思考一下,得出的结果可能就有一点区别。本文想从嵇康最后弹的《广陵散》的角度来看着个问题。 史书载嵇康曾得《广陵散》于一个隐者,并允诺不再他传,后来袁孝尼等人想学都被回绝。临行前想到《广陵散》将要失传感到有点遗憾。 《广陵散》是古代一首大型琴曲,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为东汉后期。一般的看法是将它与《聂政刺韩王》琴曲联系起来。《聂政刺韩王》主要是描写战国时代铸剑工匠之子聂政为报杀父之仇,刺死韩王,然后自杀的悲壮故事。关于此,蔡邕《琴操》记述得较为详细。 在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 这个“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反而成了《广陵散》的曲情。虽然故事情节与史书的记载有太多出入,但《广陵散》一曲主要表现的内容,如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等,并未因故事的走样而减色。 今存《广陵散》曲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编印的《神奇秘谱》(1425年),谱中有关于“刺韩”、“冲冠”、“发怒”、“报剑”等内容的分段小标题,所以古来琴曲家即把《广陵散》与《聂政刺韩王》看作是异曲同名。清末刘鹗在扬州得到这个谱子,由琴师大兴人张瑞珊整理恢复,刻于张所著的《十一弦馆琴谱》之后,现有传本。 《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四十五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主要是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全曲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和发展、变化。一个是见于“正声”第二段的正声主调, 另一个是先出现在大序尾声的乱声主调。正声主调多在乐段开始处,突出了它的主导体用。乱声主调则多用于乐。 正因为嵇康临刑索弹《广陵散》,才使这首古典琴曲名声大振,一定程度上,《广陵散》是因嵇康而“名”起来的。但所谓“于今绝矣”则非指曲子本身而言,它主要反映了嵇康临刑时的愤激之语。事实上,琴曲《广陵散》经《神奇秘谱》保存,一直流传到今天。嵇康在音乐理论上也有独到贡献,主要表现在嵇康对琴和音乐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嵇康与儒家传统思想相左的看法。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声无哀乐论》。嵇康一向主张音声来源于自然的本质,而与喜怒哀乐等主观情感无关。反对礼教音乐治世的观点。 可是我们从曲子本身来看,却是表现出“雷霆风雨”和“戈矛纵横”的气势,毕竟曲为心声,嵇康在那个行刑关头怎么会神气不变,怎么会出现前面那样的描述呢?——“风儿轻轻,琴声悠扬,围观的人群屏气慑息,谛听着神秘的旋律、生命的绝响。”这种描述纯粹是想当然的说法。 另一种视角,史书说嵇康临刑前,唯有叹息《广陵散》之不再传,可是以前嵇康本人认为《广陵散》不传别人,是很坚决的。人之将死,其心也真。可见他自己曾经很矛盾的行为,在临刑前暴露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有人说他临刑前对于《广陵散》“有点遗憾”其实,何止啊!嵇康是一个很懂音乐的,也是一个酷爱音乐的人。资料表明嵇康曾经有一张非常名贵的琴,为了这张琴,他卖去了东阳旧业,还向尚书令讨了一块河轮佩玉,截成薄片镶嵌在琴面上作琴徽。琴囊则是用玉帘巾单、缩丝制成,此琴可谓价值连城。有一次,其友山涛乘醉想剖琴,嵇康以生命相威胁,才使此琴兔遭大祸。 想一想一个如此酷爱音乐的人会真的肯让自己临死不忘的《广陵散》“于今绝矣”吗?我们可以作出推测,就是“于今绝矣”说得并不是《广陵散》(事实上也并没有绝),而是嵇康的激愤之语,再也没有像他这样的铮铮士人弹奏《广陵散》了。《魏志注·康别传》“载康临终之言,盖康自以为绝妙时人,不同凡响……以此从此以后,无妇续己者耳。”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开为什么嵇康为什么生前不曾传《广陵散》的原因。这是因为从广陵散的内容来看,是反映刺杀韩王的,也就是直接对当政者的暴力反抗,过去嵇康虽然从《与山涛绝交书》中看出他的摆明了与当政者的关系,但是很明显这种关系也仅仅在“不合作”的层面上,而并没有上升到直接的像《广陵散》中的那样暴力反抗。这也就很清晰表明嵇康本人的政治立场。这就容易让人想到当阮籍的儿子想学他时,阮籍所采取的那种果断的态度。嵇康也是基于同一种考虑。《广陵散》的那种气势滂沱,那种难以抑制的激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嵇康自己的声无哀乐,清淡,喜怒哀乐不外露相左。可是我们知道,嵇康自己也有反抗礼教,反抗当时政治那种充满激情的一面……等等的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他身前不传《广陵散》,死前后悔的矛盾中读出很多。这也是人感性好恶同理性思辩永恒矛盾的地方。难道这些积郁于胸中的不平,难道曲目《广陵散》中的“冲冠”、“发怒”、“报剑”在他临刑前尽兴弹奏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豪迈,愤怒,慷慨,嵇康自己就没有融入其中?这些还能够表明“神气不变,索琴弹之。”?依我只见,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并非“不变”,在他的内心深处,从他的琴音当中表现出来的也决不是神气不变。所以古人的在这里表述不一定非常准确,这个有嵇康自己弹的曲目,以及曲目的内容佐证。 伟大的光环下,必要有一颗伟大的生命来承担这种光环的沉重。我们可以感慨系之,可以由衷敬之,也可以操志行之,但是神而化之,总是不太好的。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丝毫不能否认嵇康在文化精神上的独特意义。